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陈悦 实习生 李晨蕾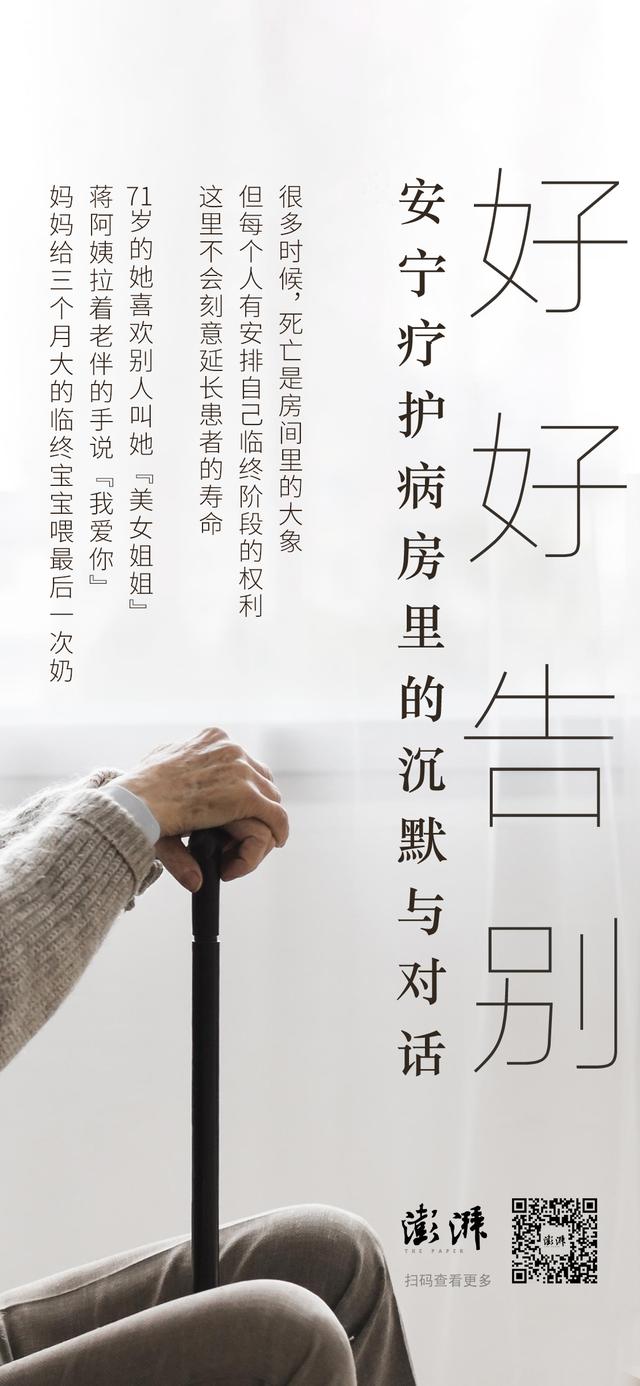 文章插图
文章插图
吴思敏 设计
安静笼罩着3月23日下午的安宁疗护病区 。
这里位于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, 26张病床住了17个人 , 大多在床上睡着了或昏昏欲睡 , 个别家属陪在床边 。 有家属形容 , “来到这 , 就是一只脚踏进死亡线内 。 ”
安宁疗护 , 又名临终关怀 , 这里的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约25天 , 有的送进来没几个小时就走了 , 很多人除了躺着 , 根本没力气做其他事 。
很多时候 , 死亡如同房间里的大象 , 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, 却避而不谈 。 但安宁疗护的医护、社工、志愿者倾向“捅破这层纸” , 告知病人真相 。
这里注重陪伴关怀 , 但不会刻意延长患者的生命 , 选择这项服务 , 病人和家属需要面对生命的抉择:
这是等待死亡吗?
延长生命和提高生命质量哪个更重要?
生命中真正要紧的是什么?
每个人 , 是否应有安排自己最后一程的自由? 文章插图
文章插图
经过装修 , 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宁疗护病区于2021年3月1日重新开放 。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陈悦 图
“美女姐姐”
徐兰 , 71岁 。 她一直在睡觉 , 直到妹妹来看望时才醒来 。
十几年前她和乳腺癌战斗 , 近三年又和子宫内膜癌抗争 , 目前癌细胞转移到淋巴 ,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状况 。
“三年了 , 化疗的钱用光了 , 住院没用 , 身体也吃不消 。 ”妹妹说 , 由于肿瘤压迫神经 , 有一回姐姐在昏迷中咬断了一点舌头 。
病床前侧摇起 , 枕头垫在背后 , 徐兰静默地坐着 , 眼神低迷 , 面容干瘪发黑 , 一顶帽子遮住光光的脑袋 。 其实 , 她喜欢别人叫她“美女姐姐” 。 妹妹找到一张她的结婚照 , 是她后来和丈夫补拍的 , 约摸在四五十岁时 , 照片上的她细眉细眼 , 头发浓密 。
“姐姐 , 好吗?”妹妹给她喂百合糖水 。
“好的 。 ”她小声嘶哑回道 。
“今天没昨天好嘛 , 今天眼神也不对 。 ”妹妹说 。
“好啊 。 ”她机械地回道 。 病房陷入长久的沉默 。
这里是上海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楼 , 走廊上偶尔有人经过 , 房顶的两条黄色光带衬得这里格外柔和 。 米黄色墙壁内嵌着一扇扇浅绿色门框 。
门框背后 , 生命试图以最舒适的方式度过最后时光 。 文章插图
文章插图
王善英躺在靠窗的病床上 。
与徐兰一床之隔 , 97岁的王善英躺在靠窗的病床上 , 淡绿色的鼻导管不间断输送着氧气 。 窗外阳光正好 , 她觉察到有人来了 , 从被子里伸出左手 , 想把遮挡视线的棉被向下压一压 , 眼神努力瞥向来客 。
她头发花白 , 精神状态却很好 , 偶尔嘟囔一两个词 , 儿子王建强也不大听懂 , “她脑子清楚 , 但表达不出来 。 ”
2020年11月23日 , 王善英发现自己说话不太流利 , 音调也变了 , 诊断结果是房颤并发脑梗 。 三天后 , 她彻底不能说话 , 右半边身体瘫痪 。
她先在医院和护理院呆了3个多月 , 一大半时间都在扎针输液 , 右手肿胀 , 难受时就一直哼哼 , 子女们决定送她来做安宁疗护 。
“康复是康复不了了 。 ”王建强说 , “她这个岁数也算是高寿 , 我们只要她平稳走好最后一段就可以了 。 ”
王善英现在每天吃8粒半药片 , 服用冲剂 , 24小时不间断吸氧 。 儿子每天都来照顾她“她最近饭量见长 , 可以吃一整碗米饭” , 有天社工来陪她聊天 , 王建强发现妈妈竟然笑了 。
安宁疗护病房 , 主要接收癌症晚期患者和老衰病人 , 医生、护士、社工、护工和志愿者组成一支团队 , 协作给予患者身体上的舒缓、心理上的慰藉 , 帮助他们坦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。
住进安宁疗护病房 , 有人是主动选择 , 有人是走投无路——其它医院不收了 , 在家没办法了 。
医生黑子明从2012年起从事安宁疗护 , 他接触过很多患者抱着怀疑态度进来 , 直到身体疼痛缓解 , 才慢慢信任医护人员 。
他说 , 这里既不会刻意延长患者的寿命 , 也不会撒手不管 , 而是有选择性地积极治疗 。 在技术手段之外 , 安宁疗护更多的是陪伴 , 是关怀 , 这有时比药物更重要 。
死亡不再是“房间里的大象”
大多安宁疗护病人都明确了终点——生存期在三个月内 。
- 野生植物|若你在山上有幸见到它们,请好好珍惜,药用价值极高,可遇不可求
- 告别人潮拥挤!济南市中心医院体检预约功能上线
- 染发剂|实锤!染发会增加患乳癌风险,年前还能好好染个发吗?丨“乳”此治疗
- 其实幸福从未缺席,只需我们好好感受!
- 高蛋白食物|患有糖尿病,把此物当“零食”吃,胜似胰岛素,告别“药罐子”
- 肌腱|告别“手机手” 多练习“指上功夫”
- 人老了,寻一隅安宁,快乐地活!
- 及时告别没有错
- 城府深的女人,有这些表现,遇见就要好好珍惜
- 牙周炎|【健哥说心脏】好好刷牙吧!为了你的心脏!
